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深蓝观(ID:mic-sh366),作者 | 谭卓曌,编辑 | 王晨,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2023年岁末,在生物制药尚未散尽的寒冬中,中国创新药领域最大的授权交易额诞生:8亿美元的首付款(约合57.4亿人民币),其合同总交易额最高可达84亿美元(约合599亿人民币),主角却是人们印象中的“做仿制药出身的公司”。
合作方是跨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为寻找到符合其肿瘤发展战略的战略性管线,它把眼光放在了在ASCO上有闪耀数据的双抗ADC,BL-B01D1上面。
12月12日,中国公司百利天恒将双抗ADC新药BL-B01D1的中国外全球权益授权给百时美施贵宝,创下了今年国产创新药“license-out”的最高金额。更为重要的是,这笔交易中,百利天恒采取了与多数中国药企不同的出海模式——“license-out+co-development+co-commercialization+全球生产供应”。
百利天恒是一家四川企业,1996年成立,做仿制药出身。创始人朱义,虽然在国内受过顶级学府的生物学训练,但他后来做过房地产、开办仿制药厂,不像圈内印象中的创新药创始人的形象。即使,他早在2014年,就在西雅图开设了创新药研发中心。
因此大洋彼岸的科学家,甚至国内创新药圈里的人,对于从未在海外求过学的朱义印象十分模糊,仅仅停留在,他是一个四川仿制药企老板。
即使他和他一手缔造的百利天恒,今年年初在科创板上市后市值一路高涨,朱义成为了今年的大黑马。10月13日,百利天恒实控人朱义因为持股市值达到281.30亿元,成为科创板的新首富。但在国内外的投资人眼里,这种非头部、创新管线非主流的公司,“是看都不值得看的资产”,一度,它的高涨都备受质疑。
为何这样一家没有多少海外科学家光环,以仿制药起家的企业,却搭上了跨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的ADC列车?
18年后,才被证实不是一个谎言
朱义在百利天恒、西雅图公司,都不是一个“甩手掌柜”。他是一个天天和科学家、原始数据打交道的创始人。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如果学习成绩好,其实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做科学家。”他在四川内江的一个工厂里长大。上世纪60年代,这样的工厂是一个封闭,却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工厂的孩子大多数的人生轨道是接父母的班。朱义是那些孩子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1980年,17岁的朱义考上了四川大学无线电专业。四年后,他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物理学,成为了那个年代顶着光环的硕士生。
然而,他的人生在当科学家的路口却拐了弯。24岁的朱义,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和同学一样出国读博士、博士后,再去做科学家。他被分配到华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当老师。
当时的的基础医学院,几乎不具备科研的条件。做蛋白质分离实验,电泳仪是坏的,朱义得自己去修,修完以后,生怕电泳仪再坏掉,就得一直守着实验室的电泳仪。实验室连椅子都没有,他就把几张圆凳靠着墙摆,经常在圆凳上面睡一宿。学院没有钱买实验所需试剂、仪器设备。就连检索国际最前沿科学讯息,在当时都极为困难。
在基础医学院任教5年之后,朱义心里的科学家梦却越来越遥远,如果还在高校继续待下去,除了职称提升之外,自己和国外同学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1992年,全国掀起公职人员下海潮,朱义也在其中。华西对于他的出走颇为意外,“建校以来,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只有我们想开除,没有自己想要走的。”
朱义自认为很简单的想法,即便现在,在旁人看来也匪夷所思——他想下海去挣钱,等迅速挣到钱,再用挣来的钱,去回归基础研究。
这条他口中的“曲线救国”路,可能在18年后的今天,才有人相信。
一开始,朱义和自己的妹妹在成都温江的柳林镇,一间租来的废旧仓库里,创办了一家叫做“新博科技”的公司,想做医药代理的生意。但并不顺利,朱义透露,“有一年腊月二十八,公司账上只有一万多块钱,工人们把他围在办公室讨钱过春节。”因为经营理念不同,朱义后来选择离开新博科技,辗转到了沿海,后又回到成都。那时全国房地产很热,他从房地产中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这段房地产从商的经历,并没有成为他人生中值得回忆的高光时刻。从复旦毕业的硕士生,到四处求人的生意人,知识分子的尊严感一度丧失,但也训练了他“生意人”的素质:对人性和社会的多元性更加理解。而“了解人性,对做企业极其重要”。
百利药业刚建的时候,朱义的房地产项目还没有收缩,由于房地产本身占用了大量资金,公司的资金链极为紧张,那一年差400万元才能运转,四处筹钱、焦头烂额之际,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贵人,一个银行行长,在调研企业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时,愿意提供贷款和支持。得知银行愿意贷款的那一天晚上,朱义和往常一样,和工人们一起住在工地上。一位工人日后告诉他,他那天半夜做梦坐起来,嘴里呢喃的是,“400万,我一定会还的。”这是朱义创业之初的心魔,“没有钱,企业怎么办。贷到了钱,又怕还不上。”
仿制药企百利诞生,大卖产品的辉煌和危机
在成都温江的医学城里,有一条长为几百米的百利路,因为百利药业是第一家在此落户的药企,因而得名。
1996年,朱义放弃房地产行业,下决心去建药厂,百利天恒的前身百利药业就此诞生。这一年,距离朱义从复旦毕业已经过去10年。这十年里,朱义以为赚钱就能回归基础研究。33岁的朱义赚到钱了之后,却发现在科研中,钱是基本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基础研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即便有了5000万的投入资金,也要去依托一个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才能有平台基础。
他意识到,自己“回不去了。”做仿制药比房地产,更接近他的专业,离他的梦想看上去也近一些。
早年,国家并未开放民营企业办制药厂。如今能叫得响名号的大仿制药企,前身几乎都是国有制药厂改制而来。朱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背景,只能在工商局先注册了百利药业,一边继续从事房地产,一边等待时机。两年后,国家放开了口子,他花了600万,把一个租来的仓库改建成药厂。
设计厂房时,设计院拿出来的方案不适合药厂,朱义拿出当时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研究,指导文件写得很简单,但它背后的逻辑,他看完也明白了大概。工厂买了一些生产设备,但厂家调试不好,朱义就自己来,趴在机器下面,自己把它调试好——这和他日后做创新药的思路一致,不脱离一线,“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做,就做出来了。”
当时,江苏一家药厂有好几个药品批文要出手。百利药业的资金只够买一个批文,要在抗病毒药和抗生素之间做一个选择。朱义在华西的专业是乙肝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他选择了生产自己更有把握的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
百利推出了第一款仿制药,利巴韦林颗粒(商品名新博林)时,市场上已经有几十家药企在竞争。朱义倾向用调研数据来指导销售,他去调研医生的用药习惯。在把四川省的大医院全部走访完后,他发现哪怕是大医院的医生,百分之七十都认为孩子感冒得先用抗生素,而不是抗病毒药物。于是,他要求销售团队做了大量关于感冒发病机制的科普和培训。第一年,新博林实现了200多万的销售收入。
新博林真正的崛起,是因为2003年非典疫情。当时,朱义被困在了北京,他从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专家称,这一次,非典的病原体应该是支原体,用红霉素类治疗即可。但病毒学的背景知识告诉朱义,非典应该是病毒感染。他立马打电话通知工厂,大量采购利巴韦林的原料药,有多少,买多少。钱不够,就去银行贷。买到之后,工厂24小时不停工,加班生产。
两周以后,香港中文大学确认非典属于病毒感染,利巴韦林是其中的推荐治疗药物之一。
新博林那一年的销售额上亿,成为全国销量最好的利巴韦林制剂。更为重要的是,非典过后,百利借由新博林打通了全国的销路,与各个医药公司建立了非常好的渠道关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品牌护城河。“我们把大量的上游原料药生产成制剂后,成为了当时疫情期间主要的药物供应企业,各地医药公司为疫情储备用药,纷纷涌来我们公司采购。来买的时候,我都想方设法让他们都能从我这拿到药,回去好交得了差。”
然而,质疑声也不断,同行认为百利在发国难财,政府也组织调查过百利。对此,朱义回应道,当时国家允许被列入疫情用药名单的药品可涨价百分之十五,但因为自己提前买入了原料,控制住了生产成本,所以百利一分钱都没有涨。“用自己的知识来做出判断,是应该赚的钱。在特殊环境,为了追求更大利润去涨价,是不该赚的钱。”
从商战中厮杀出来的新博林,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其后几年,百利天恒和其他国内仿制药一样,布局化药仿制药和中成药,把握住了仿制药的黄金时期。其年销售额稳定在十亿元以上,每年有七、八千万的现金流稳定入账。2010年前后,国内的仿制药和创新药环境也在悄然改变。
2010年春节,朱义在公司致辞中提到,“世界上只有两种药,仿制药和创新药,没有第三种,而仿制药的利润将会下降到比刀片还薄。”他认为,是时候去做创新药了。
“一个做仿制药的凭什么能做创新药”
2010年,国家卫生部七部门联合印发《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其中规定:实行以政府主导、以省(区、市)为单位的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但省级主导的药品招采,涉及到保护本土企业就业与税收,降价幅度在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在温和的降价政策中,侥幸者抱着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想法,认为全国招采一盘棋到来,还为时尚早。
但是,朱义利用模型计算,对未来做了极端情况的预测。如果国家统一集中采购,只有一个买家中标的情况下,药企毛利大概率在百分之十左右。这个模型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产品在同一个评价标准内,即同质化。
当2015年前后,国家真的推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时,巨大的危机笼罩在了那些曾经抱有侥幸心理的仿制药企身上,经历了多年无序竞争、暴利增长后,它们不得不面对降价与洗牌的命运。百利也不例外,在药品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多种政策影响下,百利的仿制药业务营收下滑。利巴韦林颗粒此前收入持续保持在6000万元以上,如今产品销售额已经萎缩至不到3500万元。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丙泊酚注射液这些产品的销量同样在下滑。
2018年至2021年,百利天恒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1.11亿元、12.07亿元、10.13亿元和7.97亿元,同期净利润分别为3282.89万元、774.23万元、3792.29万元和-9999.13万元。到了2022年,亏损进一步加大,营业收入仅有7.03亿元,净利润为-2.82亿元。
在这样的财报面前,没人会相信这样的仿制药企会在创新药领域创出名堂。而实际上,早在2008年,朱义已开始涉足创新药。
2008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启动。专项针对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十类重大疾病,研制一批重大药物。朱义和上海的高校、研究机构合作,一共花了500万元,拿到了两个国家新药创制的研发项目,一个是研发用于治疗肝癌的药物,一个是研究用于治疗淋巴瘤的融合蛋白。他还从一家日本药企,引进一款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
遗憾的是,2013年,三个项目全部宣告研发失败。
药物研发的失败,并没有影响朱义在上海建研发中心的计划。2008年后,跨国公司陆续在上海张江建立研发中心,一批海外科学家随之回国,而其中,就有朱义曾经在复旦的校友们。朱义去调研拜访了一些海归科学家,其中一些人基于当时中国创新生态的现状,建议这样一个商业故事——选择一款辉瑞或默克正在做一期临床的新药,稍微改一改、绕过专利限制,当它们做到二期、三期临床的时候,再及时跟进一期临床。如果它们失败了,就立刻停止研发,成本不会高。如果它们成功了,我们是跟得最紧的。
听完这个故事后,朱义很失望,他认为这种做法没有创造性。所讲述的故事本质无非就是,花更高的成本,做一个更高端仿制药,在更高端的市场上贴身肉搏。而自己之所以从仿制药转身,就是为了脱离这种肉搏。
当朱义追问有没有辉瑞、默克等跨国药企都没有做、但临床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创造性的东西,是否我们自己来做?
当时大家认为朱义的想法不切实际,国外新药研制动辄耗时十年,花费十亿美金,你一个仿制药企的老板,一年利润只有六七千万元人民币,凭什么去做真正的创新药?
朱义对此并不服气。在他看来,十亿美金,只是一个统计数据。多年做企业的经验告诉他,很多时候别人觉得做不到的事情,真的下定决心去做,也不一定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我不会去收购一个公司,我要一个一个去招”
在上海寻觅了两三年,朱义一无所获。
2013年,他去了两次美国,将波士顿、湾区、圣地亚哥等几乎所有主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全都参观了一遍。他去听诺贝尔学者的讲座,去看二十几人的Biotech公司如何运行,和美国的前沿教授探讨哪些靶点值得开发。
朱义这才发现,原来在美国的医药生态里,要做创新药公司,二十几个人就够了。并不是像跨国药企在上海一样,一栋楼,一家公司,几百上千号人。Biotech长成什么样子,大概多少人,怎么样去运营,从企业运营角度,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公司一年成本在5000万到8000万,或者一个亿的人民币,自己还出得起。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朱义就在关注创新药的前沿领域。他一直有一个三五人的团队,用来跟踪前沿研究、检索文献。这个团队不在仿制药体系内,相当于专门的“信息检索部门”。他们会定期把文章和数据整理好,发给朱义阅览。尤其是肿瘤抗体类药物最前沿的靶点,一个靶点一个靶点去筛。靶点本身的生物学研究,每一个月会更新一次,如果有新的研究文章发表出来,那么朱义会和他们一起把文章拿出来,深度去解读它。
数十年如一日,因而,朱义对于成药性比较好的、工业界在做的靶点,并不陌生。他形容这些年自己属于“没吃过猪肉,但是一直在关注猪怎么跑。”
2013年,初次到访美国时,美国正值生物医药寒冬,西雅图很多生物医药公司有计划关闭研发中心,安进、诺和诺德、百时美施贵宝都在收缩规模。既然这些公司都在裁减研发人员,那自己正好可以在西雅图低价租试验室、买二手仪器设备、招科学家。2014年,一过完春节,他立马启程去美国,在西雅图成立了一家聚焦肿瘤类药物研发的创新药企——“Systimmune.LTD(西雅图系统免疫)”。
受益于当时西雅图的裁员潮,那些失去工作的科学家,起码愿意到朱义的公司看一眼。但是,前来面试的研发人员,一听到他的介绍,得知这是一家中国仿制药企背景的公司时,他们几乎都是质疑。“你们原来做仿制药的,在美国没有任何背景,知道如何做创新药?”也有英国籍的科学家向朱义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到一家中国公司工作,如何解决文化冲突。
他回应:“做创新药并不在乎自己过去做什么,不在乎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关键是人够不够有智慧,是不是有创新意识;至于文化冲突,既然是做创新药研发的,就应该基于科学数据来交流沟通,Systimmune的文化就是基于科学数据驱动。”
不知是被朱义的理念打动,还是迫于现实的Biotech寒冬,西雅图系统免疫公司吸引到了不少与他同频的研发人员。他们大部分为美国本土科学家,也有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印度的科学家。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特质,一看到数据,两眼放光。遇到一个难题时,能迅速拿出解决方案。在朱义看来,这,就是基于“数据兴奋”的同类相吸。
百利扬帆出海时,国内正在经历汹涌的海归潮,创新药发展烈火烹油,归国博士们身价水涨船高,常常被炒至千万年薪。朱力远离了这一波行业内卷,2014年底,他的创新药团队组建完成,十几人的科学家团队人工成本约2000万,总成本在4000万元左右,这都远低于他的预算。
他开始把国内仿制药的销售、生产和财务全部交由国内团队管理,对于这块业务的预期,是保持企业平稳运行,保证两、三千人的就业,可以继续反哺创新药。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创新药的研发上。每隔两三个月,他都会在美国待上两周。在国内的时候,他是每天上午8点到10点,和美国研发人员开远程视频会议。会议内容只有一项,讨论研发的数据。
在对创新药公司的管理上,核心的试验设计,他都参与其中。一线研发人员对数据整理分析完后,必须第一时间将一手数据告诉他。朱义不允许到他手中的是,经过层层汇报、人工筛完后的“多手数据”。
他是一个对于数据十分敏感、并且极其关注的人,一个双抗曾经交由一家CRO公司做安评试验,拿到数据后,他第一反应觉得数据不太对劲,便要求重新拿出原始数据来,一比对,还真是数据出了问题。
在西雅图系统免疫公司里,如果有一个顶着很高的头衔的科学家来告诉他,我不做试验设计,只做管理。朱义会态度坚决地拒绝,原因就是“我们连共同语言都没有。”但如果对方扎扎实实地做科研并拿出好的数据,兴奋地拉着他一起看数据,他会激动不已。
这个靶点,难道不是一个笑话吗?
在西雅图系统免疫公司筹备时,2014年初,朱义写了一份公司未来十年规划的手稿,他想要去做双抗、多抗、ADC药物——这些靶点至今在行业内看来都极为另类,在2014年的美国,也是足够前卫。很多同行甚至认为这是一家“无厘头”的公司。
他们的质疑完全合理。2000年,辉瑞研发的全球首个ADC药物获批上市,由于没有解决毒副作用问题,它在2010年又主动撤市。2014年,TDM1上市并未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直至2019年,第一三共研发的DS-8201展示了颇为亮眼的临床数据后,ADC药物才被认可与追捧。
朱义却在2014年,ADC药物在美国正处于低谷时,提出要去做双抗ADC。这遭到了部分内部研发人员的质疑,大家认为,单抗ADC毒性问题都暂时没有解决掉,双抗ADC的不确定性只会更高。朱义却坚持,“Try,Try,Try!”是公司在管线选择时,朱义经常和员工争论不休的口头禅。在他的思维世界里,他不理解一个事情连试都没试,就说不能做的行为。“先做出来看,真的走到那一步,真有这么大的毒性,错了,再说。”
当自己的研发人员一听到,朱义要去做一个像钢铁侠一样的四特异性抗体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笑话。”他们更坚持去做双抗。每每到了争议、分歧的路口,研发人员坚持自己的意见,朱义采取的办法是,给他们一半资源,让他们按自己的思路做,同时自己也留一半资源,按自己的思路做,两条路走出来看看。
当大家都在做单抗的时候,他的底层逻辑是,已经意识到单抗的有效性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用多靶点攻击它,要么用更强效的效应器去大规模杀伤、攻击它。前者就需要双抗、多抗。而后者,当时已经有大量研究显示,ADC和Car-T技术将会是非常有潜力的候选技术,只是当前技术并不成熟。
既然如此,把技术问题解决掉就好。无非是需要时间和投入:如果出现了风险,就去加强风险承受能力;资源不够,那就再去思考怎么把资源找回来。
反倒是技术之外的问题,他会根据现实选择。Car-T,曾经也在他计划之列。但调研一番后发现,自己手上的钱,是难以支撑在美国做Car-T研究的费用,而西雅图系统免疫公司又不具备做Car-T研究需要的临床医生资源。于是,他放弃了这一想法。
创新的现金压力还是到来。据招股书显示,2019~2021年及2022年1-6月,百利天恒的研发投入分别为1.81亿元、1.96亿元、2.79亿元、1.73亿元。百利天恒在研发上的投入逐年增加。但国内仿制药的利润逐年下降。
2019年,国家第一次药品集采,并没有让百利天恒伤筋动骨,仅仅是一款小产品被纳入集采之中。但2021年,百利天恒丢掉了大单,主打产品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在集采中失标,销售归零。
仿制药利润一旦下滑严重,创新药发展的支撑就会断裂。“那个时候,压力真的很大。”2017年,他开始未雨绸缪,从外部寻求资金,为创新药失败做资源准备。美国奥博资本很快给西雅图系统免疫公司投了一笔资金。但朱义花得很谨慎,到2022年,BL-B01D1进入临床试验以前,钱一直趴在账上没动。
好在科创板给企业打开募集资金的通道。百利天恒在2019年初就筹划上市,几经波折,终于在今年年初上市成功。
收获期,百时美施贵宝的交易
2023年6月,百利天恒受邀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上汇报BL-B01D1的首个人体临床I期研究数据。BL-B01D1,正是在2014年不被看好,但百利天恒研发的双抗ADC。
但2023年开始,ADC就成为全球BD领域的大热赛道。
数据一旦亮相,相当惊艳。结果显示,在可进行疗效评估的139例患者中,中位随访4.1个月时,整体客观缓解率(ORR)为45.3%,其中EGFR突变型NSCLC的ORR达到63.2%、EGFR野生型NSCLC患者的ORR为44.9%、NPC患者的为53.6%。
美国大PI直接在会场找到朱义,希望参与在美国的临床试验。
全球排名前十的跨国药企中,有8家跨国药企主动寻求合作。一些药企想做lisence-in,简单买断BL-B01D1,这遭到了朱义的委婉拒绝。在朱义的构想里,出海是三步路,成立西雅图免疫公司后,再是临床开发、商业化落地。第一步,已经完成,第二步已经在建,算是步子已经迈出去了。既然要往前走,在与有意愿合作的跨国药企沟通时就明确,百利在BL-B01D1的策略是一定要全球化,一起来做临床研发、商业化推广。
百时美施贵宝在会场密切关注着BL-B01D1的数据,这家MNC巨头也面临着所有跨国药企一定会经历的挑战:2014年7月,百时美施贵宝O药率先在日本上市,成为全球首个上市的PD-1,并稳坐三年PD-1老大的宝座;默沙东的K药也在同年上市,但一直被O药死死碾压。2016年,K药销售额为14.02亿美元,而O药销售额达37.74亿美元,超过K药近2倍。
K获批肺癌一线疗法后,O药自此败北。2020年,O药销售额首次下滑,只有69.92亿美元,但K药销售额已达143亿美元。此后,O药通过联合Y药,获批肺癌一线疗法,但由于疗效优势不明显,再次失去先机。
在O药奋力追赶K药之际,全球跨国药企开启了ADC收购之战。在拥有PD-1之后,似乎谁都想拥有一款ADC。毕竟ADC与PD-1联用能取得更显著的临床效果。默沙东、葛兰素史克、阿斯利康、艾伯维、辉瑞等,从去年开启疯狂购物模式。
反观百时美施贵宝,在这场扫货大战中,晚了那么一点。今年4月,百时美施贵宝从德国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手里以10亿美元的首付款买进ADC。11月,再以1亿美元的预付款从韩国引进一款ADC药物。
如果再买一款单抗ADC,对于百时美施贵宝而言,意义不大。既覆盖不了这么多适应症,也形不成这样强势的竞争地位。当百时美施贵宝选择BL-B01D1时,在国外行业媒体评价道,百时美施贵宝迫切需要去开辟了一条新的ADC战线,这条新的战线可以和吉利德、辉瑞在ADC上竞争。
与百时美施贵宝的合作,“对百时美施贵宝来讲,找到了与其战略相匹配的战略性资产,对百利天恒来讲,获得了实现出海全球化的重要的、重量级的合作伙伴。”朱义很满意这次合作,而且百利天恒也有了更充足的钱用于研发。
为什么会是百利天恒和朱义?
在百利扬帆出海的这一段时间,国内有很多仿制药企纷纷成立研究院,或者是在美国建立研发中心。一位曾经被派往在美国新泽西的研发人员回国后讲述了这一段经历,自主研发这条路走起来太难,多数在海外选择更容易的捷径:引进已经在做的临床一期项目,把它做到临床二期后,再转让出去。
但是,只要牵涉到临床,就意味着等待与投入。国内的营销团队对研发缓慢质疑不断,加上医保目录调整、国家药品集采的风声传来,原有产品可能被踢出医保。向来力主创新的老板,考虑当下企业生存,最终撤掉了海外的研发点。
朱义没有在国外走“lisence-in”路线。他认为,中国仿制药企能够从海外买到的产品,几乎都是被挑剩下的。而真正好的产品,自己是买不起的。
他也没有跟其他到美国的中国药企一样,为了快速搭建团队,去美国收购一家创新药企。反而是亲自去面试科学家,建立研发团队。在他看来,收购过来的技术团队,如果不认可公司理念,并购组成的团队很快就会散掉。这样,收购的价值就只剩下公司原有的专利,如果这些专利是过时的或低价值的,收购就立刻毫无意义。只有自己亲自招进来、培养起来的人,才会是自己的科学团队。国内创新药团队的人才建设,也是朱义直接从学校招人,从一张白纸开始培养他们。过程看起来慢,核心团队一旦建成,它就会非常高效在运转。
在他看来,中国仿制药企要转型,要么做成一个巨无霸,在拥有非常多的资源之后,去并购一个已经成型的创新药体系、或者花与MNC同样大的价钱去license— in 真正的创新药,但绝大多数仿制药企的体量都不够。要么就是老板自己有创新能力。但是,大多数仿制药企在转型中做法是招一个曾经参与过创新药研发某些环节的人。一个创新点出现时,这些人在过去只是参与其中的具体操作人员,并不是真正能够拿出创新想法的总设计师。“而总设计师,在美国都贵得不得了,资本都围着他转。他又怎么会任职于一家仿制药企?”
他选择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自己带队,自己做药。
凭借所持有的百利天恒的股份,朱义如今成为了科创板的新首富。这个称谓对他来说,不如“新药研发人员”这个身份更真实。当看到临床数据出来一个PR(当患者的肿瘤缩小了30%以上,但没有达到完全缓解的程度时,可以被称为PR),说明有药效时,这更让他感到兴奋。
与百时美施贵宝交易消息公布之后,他出去做报告的时候,听到的不再是诟病、不理解,反而有更多同行,当面对他说,“你这两个靶点很好,我们也在做。”
在近二十年的务实、冒险,刺激和稳定的漫长平衡中,朱义感觉自己此刻最贴近“科学家”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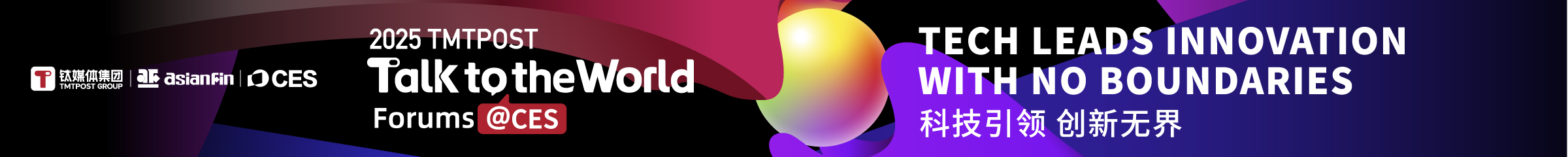


 快报
快报
根据《网络安全法》实名制要求,请绑定手机号后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