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砺石商业评论,作者|金梅
一个药企想要在世界药坛立足,往往需要一款重磅级药品为其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比如拜耳的阿司匹林,辉瑞的青霉素,还有昔日药坛巨头诺华的“格列卫”。
格列卫作为帮助诺华跻身药企巨头的核心产品,虽然不像阿司匹林、青霉素妇孺皆知,但这款开创了世界肿瘤分子靶向治疗时代的白血病神药,在国内也曾引起过巨大轰动。
格列卫正是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让徐峥饰演的中年落魄大叔逆袭成药神的“救命药”。
作为曾经称霸药坛的公司,1996年才成立的诺华,只有二十多个年头,但诺华背后的渊源却已经足足有265年。
从最初三个从事织布、做染料、印标签,依靠在德国巨头身后捡漏存活的瑞士小厂,到在制药领域响当当的角色,诺华靠什么在新领域立足,又如何对抗强势崛起的竞争者?
化工历史
1758年,诺华的前身——贸易公司J.R.Geigy,诞生于瑞士的第三大城市——巴塞尔,销售化学品、染料原材料、药品原料等。
巴塞尔与法国、德国交界,背靠全球先进的市场,还有莱茵河这个供水、运输、排污通道,且没有德法的染料专利保护政策,让这里的纺织业发展非常迅速。
1830年,Geigy公司已经开始用手工的方式,生产传统的来自植物、动物或矿物的染料。随着瑞士染料行业的蓬勃发展,1840年,丝绸染色工厂CIBA成立了。Geigy和CIBA不会想到,此后它们的命运会息息相关。
火爆的市场需求很快催生了革命性技术,1856年,红色工业染料苯胺紫诞生于英国。1858年,品红染料被法国化学家发现。这种用焦煤油做原料制成的工业染料,比植物染料更容易上色,利润也要高得多。
英法商人很快对这种染料注册了专利保护,开始攫取巨额的垄断利润。瑞士公司CIBA通过跨国家族婚姻获得了品红染料的专利,1859年它就开始在巴塞尔的工厂生产工业染料。
Geigy公司当然不肯示弱。由于瑞士没有专利保护,1860年,Geigy公司也迅速进入了工业染料领域,并依靠其此前积累的海外渠道全球铺货。1870年,CIBA通对国内外工厂的吞并不断壮大,还通过代理公司向世界各地输出工业纺织染色剂,并为很多国家提供标签印刷。

1886年,Alfred Kern博士(1850-1893)和Edouard Sandoz(1853-1928)在瑞士巴塞尔成立化学公司。
1886年,化学家Alfred Kern和朋友Sandoz在巴塞尔建立了一家染料工厂Alfred & Sandoz(由于Alfred早逝,公司后被更名为Sandoz),一个负责技术,一个负责市场。至此,诺华家庭的三兄弟终于凑齐了。
有趣的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料到,作为三家卖染料的公司,竟然会在百年后影响全球医药产业的格局。
Alfred是个有技术的博士,加之瑞士没有专利保护的双重便利下,Sandoz次年就可以生产6种染料,1892年公司已经能生产28种染料,年产量380吨,5年产量翻了30倍。Sandoz还模仿着Geigy、CIBA开展了印刷画和产品包装等服务。
作为做“盗版”业务的三家公司,它们虽然很努力,但在德国的巨头光环下,在世界市场的存在感并不强。1894年,世界上的142种工业染料专利,德国狂揽116个,瑞士占据15个,英国和法国共11个。
但很快世界的大变局,却给了瑞士染料工业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1914年,一战爆发。占据了纺织染料业85%份额的德国,突然停止了对英国及其盟友国的燃料出口。短短两三年时间染料价格涨了十几倍,却依然供不应求。德国丢掉的市场,自然落在了瑞士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瑞士染料巨头赚得盆满钵满,但同时也培育了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染料领域的大敌。
面对对手的崛起,1918年,CIBA、Geigy和Sandoz成立了计划持续50年的垄断利益集团——Basel AG(巴塞尔有限责任公司),来抱团取暖抵御外敌(三家公司每年的利润按照2:1:1分配)。
一战后,美国用法案和高关税来扶持本国的染料化工业,瑞士的处境雪上加霜。于是他们干脆买了个美国公司,直接置身美国市场。但依据美国《反托拉斯法》,这种垄断组织是非法的。1951年,巴塞尔股份公司解体。
1970年,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来自德、美、英和波斯湾新兴化工工业的竞争,加上研发费用负担逐渐沉重,CIBA和Geigy选择合并,CIBA-Geigy诞生。

1970年,嘉基公司总裁Louis von Planta和汽巴公司总裁Robert Kappeli握手,宣布汽巴和嘉基合并。
但历史的车轮并没有给CIBA-Geigy喘息的机会。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全球能源资源和原料价格猛然上涨,很多化工企业倒闭。美国一些化工巨头如辉瑞开始把重心转向制药,多元化的制药公司也开始主攻药品研发。
化工行业大势已去,CIBA-Geigy和Sandoz将何去何从?
药物转型
这三个化工公司完全不用惊慌,其实它们早在近百年前就顺手做起了制药生意。染料工业跟现代制药业,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业务,为什么能顺手一起做呢?
1878年,一名对染料技术颇有研究的医学博士Paul,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介绍了细胞染色技术和其相应的染料。此后他开始通过染色分辨人体不同的细胞。1885年,他灵机一动,如果能给染料加上特定的病毒,那不就实现了精准治疗吗?随着专杀梅毒细菌的砷凡纳明的问世,现代医药与染料工业相伴而生。
1884年,解热止痛药安替比林在德国爆火。1895年,Sandoz通过与德国Hoechst公司合作生产解热止痛的安替比林,从中获得固定的分成,进入了制药领域。CIBA则借着荷兰没有专利的“便利”,在1887年开始仿制此药,进入制药领域。
Sandoz不只有联合生产,身在瑞士的它必然很难拒绝仿制药业务。它和CIBA都仿制起德国的处方药——工业糖精(由于德国担心糖精会影响蔗糖的利益链,所以将糖精列为处方药进行销售)。由于蔗糖利益链的限制,德国糖精的产量从每年200吨骤降到5吨。Sandoz和CIBA又一次当上了捡漏王,还顺便支持了瑞士的巧克力工业。
由于民间对糖精的巨大需求,瑞士开始向周边各国走私糖精。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糖精甚至被混入石蜡制作成蜡烛,走私到奥地利的教堂,再重新熔化蜡烛提炼出糖精。这个生意一直持续到一战中德国取消糖精的生产禁令,才划上了句号。
做仿制药的Sandoz还曾模仿其他企业,从罂粟中提取可待因,从此天然提纯也成了Sandoz制药业务的重要方向。1918年,Sandoz的科学家Arthur成功从麦角中,提取出了高纯度的生物碱:麦角碱。
1921年,麦角碱产品Gynergen酒石酸麦角胺上市,用于治疗产后大出血。此后,Sandoz一系列治疗神经紊乱、血栓、帕金森、偏头痛等疾病的药物,以及曾经让乔布斯着迷的致幻产品LSD,都是在此基础上研发的。虽然Sandoz在研发上可圈可点,但制药部门直到1924年,才首次盈利了2.7万瑞士法郎。

1924年,Sandoz推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产品——葡萄糖酸钙,这款药不但在此后多年扛起了公司三分之一的营收,还结束了补钙依靠注射和吃土一样的药片的痛苦历史,为现代钙治疗奠定了基础。补钙可以治疗的疾病太多了,以至于一位德国儿医开玩笑说:这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补钙疗法还没被使用过的疾病。
在制药领域尝到甜头的Sandoz开始了对药物领域的全情投入。CIBA在制药领域也在不断开疆拓土,1908年通过收购BCF,获得了抗真菌的氯碘羟喹。在1918年到1939年间,CIBA先后发布了8款性激素和荷尔蒙药品。
跟这两位早早寻找第二曲线的企业不同,昔日的前辈Geigy,1920年才从染料工业中分出精力,一头扎进了农业化工产品研发领域。直到1938年,Geigy才成立自己的制药研发部门,但此后在制药领域却开始弯道超车。二战期间,Geigy研发出了治疗花粉症的Privine萘甲唑啉和用于孕妇生产麻醉的Nupercaine奴白卡因。
但让Geigy成功逆袭的,却是它的农业化工产品——杀虫剂。
1939年,Geigy公司研究皮革鞣制剂和植物消毒剂的化学博士Muller,研制出了一种可以让虫子兴奋而死,对人体却无害的杀虫剂——DDT。这个药不但对提高粮食产量功不可没,对消除二战时由虫子传染的斑疹伤寒和疟疾也立竿见影。Muller因此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而Geigy则开始在行业中名声大噪。
看到Geigy的火热,1939年,Sandoz也进入农化工业领域,次年CIBA也做了战略跟进。
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医保的大范围普及,制药行业迎来了黄金发展的20年。尝到了技术研发甜头的Geigy、Sandoz,在新技术的投入上更加果断,投资效果也立竿见影。没有重磅级研发成果的CIBA,却开始有些跟不上节奏了。
1949年,Geigy的第一个重磅级药物——治疗风湿和痛风的保泰松上市,该药持续雄霸市场第一的宝座(我们熟知的扶他林,就是保泰松经过二十多年持续改进后的产物)。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Geigy治疗精神病症、癫痫和高血压的药物纷纷问世,集团收入从5亿瑞士法郎增长到20亿瑞士法郎。
1967年,Geigy销售额已经超过了CIBA的27亿瑞士法郎的年收入,Sandoz的业绩同样惊喜连连。
1963年,Sandoz通过收购Biochmie进入抗生素领域。1972年,Sandoz的科学家从挪威高原的土地中,发现了可以抑制其他真菌生长的真菌,并从其中分解出了可以“免疫抑制”的有效成分——环孢素。1983年,Sandoz的环孢素上市,用来治疗器官移植的排异反应、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等自身免疫病,成为公司的拳头产品。
制药业的一路高歌中,Sandoz还进行了业务拓展,1967年进入营养品业,1969年吸收合并瑞士染料业6巨头的最后一家Durant & Huguenin,1985年进入建筑化工业。进入90年代,又通过收购布局基因治疗领域。
在研发进程中有些掉队的CIBA,决定抓住先行者的衣角。1969年,CIBA和Geigy联合建立了菲利特里希·米希研究院,专门从事生物化学和药物基础研究。1970年,两家公司直接合并,CIBA-Geigy诞生。
70-80年代以来,CIBA-Geigy在时代的洪流中蓬勃发展,家庭消费品、种子与农化工、精密天平、疫苗、眼科……业务不断多元化,营业额稳步增长。本以为公司会在此后的生涯顺风顺水,谁料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下,农化工业的反杀虫剂/除草剂运动愈演愈烈。
其实早在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就将DDT让春天没有鸟叫,变得寂静的危害拉入了公共视野。1972年,以美国为首随后在全球宣布禁止使用DDT。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化工染料工业不但命运岌岌可危,利润也越来越低。1989年,CIBA-Geigy农化工、染料化工、制药的销售额为206.08亿瑞士法郎,但利润仅为15.57亿瑞士法郎。贡献了一半营收的染料和农药产品一旦丢失,必然使公司元气大伤降低国际地位,公司该何去何从呢?
此时,在制药领域风生水起的Sandoz,进入CIBA-Geigy的视野。
1991年12月,Sandoz收购了拥有提纯造血干细胞技术的Systemix公司60%的股权。1995年7月,Sandoz又整体收购世界基因治疗之父Frendch Anderson创立的公司Genetic Therapy, Inc.(GTI,基因疗法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在基因领域的提前布局。
彼时在制药行业,CIBA-Geigy世界排名第九,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3%,Sandoz世界排名第十四,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1%。由于竞争加剧,研发费用快速增长,制药行业发生收购合并的事件不断在上演。
想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地位的Sandoz和CIBA-Geigy几乎一拍即合。
成立诺华
为了防止地位受到挑战,1996年,瑞士巨头再次合并,诺华(拉丁语novaeartes,意为新技术)诞生了(Sandoz持股55%)。

1996年,汽巴-嘉基和山德士合并,诺华公司成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药健康企业之一。图为:1997年2月3日,工人正在更换诺华巴塞尔St. Johann工厂的旧标识。
合并后,诺华共有员工135000人,公司年销售额高达362亿瑞士法郎,总资产580亿瑞士法郎,现金和现金等价物190亿瑞士法郎。为了避免垄断的嫌疑,它们剥离了本来就视为鸡肋的旁枝业务,开始专心在制药、农化工、营养品三大业务。
剥离后公司剩余员工94000人,总营收211亿瑞士法郎,总利润39亿瑞士法郎,制药业务占总营收的2/3,利润的3/4,拥有全球制药市场份额的4.4%,超越了全球排名第二的默克,排在英国葛兰素威康之后。
在“平等合并”理念的指导下,诺华董事会和核心管理层由原两家公司的人员五五分成来担任。同时,在全公司的每一个业务部门,都成立合并专案组,一共成立了200个专案组,分析指导了近600个项目的合并。所有基层员工,都要重新提交简历和经过面试,称作“Hire-and-Fire”(雇佣和解聘)。
两种文化融合,短时间内获胜的一般是强势的一方,再加上Sandoz的持股比例更高,诺华的CEO也是Sandoz的原CEO,所以强调给员工赋能的CIBA-Geigy,输给了Sandoz的“命令与控制、强烈和清晰的责任”的管理方式。
如此一来,公司的决策、执行力提升了,3个月诺华就完成了全公司65%的业务和项目合并,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受到了限制,员工对此叫苦不休。
由于新CEO对CIBA-Geigy的业务完全不了解,还处在萌芽阶段的未来“药神”格列卫,开始变得岌岌可危。因为只能针对慢粒白血病患者,格列卫受众面太窄,大家甚至不相信这个投入了三年的项目会在未来回本。
格列卫项目的科学家Matter,气冲冲地找到新CEO,义愤填膺地批评了合并带来的混乱和低效,说服CEO不要相信市场上所说的患者人数少,所以新药价值不高的思路,只要疗效好,病人就会反复购买的。
火药味十足的Matter并没有惹怒新CEO,相反他竟然被Matter的专业和激情感染了,格列卫保住了。深知“专业和激情对研发同样重要”的CEO,甚至直接把诺华癌症研究部的将领重任授予了Matter。
格列卫的进展并不顺利,动物实验阶段本来已经胜券在握的格列卫,却突然被发现会导致血液凝固和肝脏毒素增加问题,这直接搁置了格列卫的问世。但充满了激情的Matter绝对不会就此放弃,又经过近两年的苦苦探索,制剂部门将该药的有效成分做成了甲磺酸盐,解决了溶解性难题,格列卫终于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但诺华却进入了合并以来的至暗时刻。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Sandoz的基因业务却开始连连受阻。1999年,一位接受基因疗法的病人却突然意外死亡,基因疗法步入低潮,基因疗法公司的CEO和近三分之二的员工都离职了(不过,诺华在基因业务上的坚守,让它在此后的2017年获得了FDA批准的第一款基因细胞疗法Kymriah)。
1999年上半年,环保和竞争压力让公司的农化工的销售额下降了10%到约30亿瑞士法郎。一年前,诺华在美国建立了人类基因研究机构和植物遗传学实验室,就当诺华准备在转基因市场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转基因作物却被美国调查,民众的反抗情绪也日益激烈。
农化工业绩就这样立竿见影地下滑了,制药业务也如履薄冰。诺华非常在意的美国市场,市场份额持续下跌。诺华的主力药品很多已经专利过期,公司75%的药品已经上市5年以上。
诺华被逼到了改革的道路上,它直接剥离了农化工业务,并且将剩下的弹药,全部放在了新药的研发上。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搞研发,2000年5月11日,诺华在纽交所上市。2001年格列卫获批上市,2003年其销售额就突破了十亿美元,成为公司的救命稻草。
为了应对专利悬崖后仿制药的冲击,诺华找到了非常新颖的思路:加入它们,成为它们的领导者。2002年,诺华收购斯洛文尼亚Lek公司,让其接手所有的仿制药业务。2005年,诺华收购德国仿制药Hexal全部股份和Eon lab 68%的股份。此后全球仿制药约一半的销量都是诺华旗下Sandoz的。
但仿制药毕竟价格很低,所以诺华的这部分业务不但利润微薄,营收也只能占到20%。创新药才是真正的引擎。诺华也一边在研发上加足马力,一边开始通过收购开疆拓土。2006年,诺华并购疫苗巨头Chiron,2010年,516亿美元收购眼科老大Alcon爱尔康。
1977年,雀巢2.8亿美元收购爱尔康,33年涨了187倍。但对诺华而言,爱尔康的收购却成了它事业上的一个败笔。收购来的疫苗和眼科等公司,业绩不尽如人意,更糟糕的是囊中羞涩的诺华,收入却越来越低。
2012年底,诺华第一代重磅药品Diovan专利到期,这意味着年销售60亿美元的降压药,将在仿制药的打击下,销售巨额缩水。本被寄予厚望的降压药Aliskiren,却在2011年上市四年后突然发现副作用,巨大的打击让诺华裁员1000人。
2015年,格列卫的专利到期,次年仿制药涌入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诺华该何去何从?
诺华开始重新梳理业务线,剔除业绩表现不好、增速放缓的疫苗业务、保健业务、流感疫苗业务,用卖出的现金收购了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候选药inclisran,开发出了第一个被FDA认可RNAi药物The Medicines Company和GSK的肿瘤部,加码布局更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但这些动作依然未能救其于水火,为了进一步聚焦创新药,诺华决定加速“瘦身”,除了剥离仿制药业务Sandoz外,诺华还卖出了五款眼科药物。但在对手们疯狂奔跑的时候,诺华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了前五。
2022年,诺华总营收485.1亿瑞士法郎,同比下降2%(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4%),净利润为63.0亿瑞士法郎,同比下降71%。仿制药业务Sandoz,净销售额为83.4亿瑞士法郎(同比下降4%),预计于2023年下半年完成剥离。
这么彻底地瘦身之后,诺华到底能不能迎头赶上,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不过从早期为了对抗德国垄断和美日崛起,三巨头合并,二战后为了进入美国市场断然解散,化工产业式微,三家公司再次合并,且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占据半壁江山和百年历史的化工产业转型医药产业,告别仿制药业务,押注一个并不完全清晰,但很确定的未来。对一个巨头而言,这种说断则断、不被过往束缚的果敢,的确非常值得敬佩,也值得很多企业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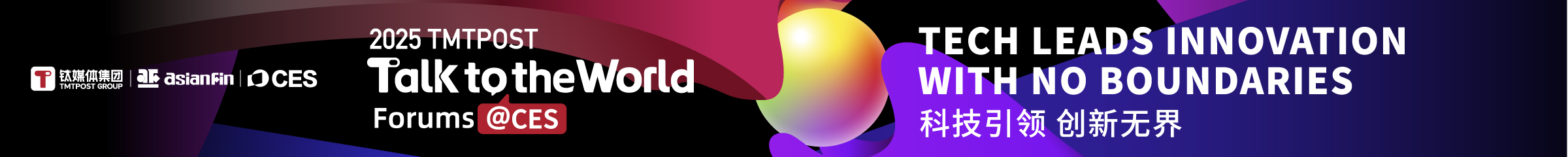

 快报
快报
根据《网络安全法》实名制要求,请绑定手机号后发表评论